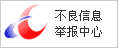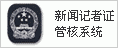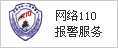我曾有機會爬到故宮養(yǎng)心殿的屋頂,見證一片片琉璃瓦被揭開、一塊塊木質構件被卸下。房梁上,那已有400年歷史的五彩祥云紋樣逐漸在我面前鋪開,我感到眼前的一切就像一扇歷史的窗戶。推開這扇窗,我的眼神與明清時期工匠的目光交疊重合了。
這一幕足夠震撼,但還不足以讓我真正讀懂這座建筑。在故宮“飛檐走壁”,只是拍攝紀錄片《我在故宮六百年》帶給我的獨特體驗之一。“沒有一座城池可以離開人存在”——更令人難忘的故事發(fā)生在故宮之外。
那是2020年8月一個周五的傍晚,得知一車從河北廊坊運往故宮的松木即將啟程,我們立刻集結,從北京向廊坊出發(fā),準備從起點開始完整記錄松木的“故宮之旅”。不料,電子導航中的路線由綠變紅,車程從預計的90分鐘拖到3個小時。最終在木工隊長和貨車司機的幫助下,我們趕在木材啟程前到達廊坊,在晚上12點拍下木材抵達神武門的鏡頭。
我們與貨車司機孟師傅共同度過了一個漫長的夜晚。在路邊席地而坐、等待限行時段結束的過程中,我們在孟師傅身上獲得了意料之外的素材。至今,他獨特的工作習慣、他與家人視頻通話時的神情,還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。這次拍攝經(jīng)歷給予我深刻的啟迪——宏偉的故宮、燦爛的歷史,與那些默默無聞的普通勞動者息息相通。
曾經(jīng),我深受影像人類學啟發(fā),樂于在拍攝的過程中不斷尋找、體悟、講述生活的真諦,讓生活這個“老師”教我如何表達。如今我更加堅信,只有進入現(xiàn)場,用一種細膩的、不帶預設的方式,才能體會并捕捉人的獨特氣質和物的豐富意蘊。
我是紀錄片創(chuàng)作者,也是紀錄片教育者。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,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紀錄片的力量。一次,我?guī)W生到福建的古村落拍作品,幾天后發(fā)現(xiàn)原本信心十足的學生突然打了退堂鼓:他們想要拍攝的主人公經(jīng)常醉酒,難以溝通,拍攝不得不停止。我告訴大家,不去預設、慢慢醞釀,去發(fā)現(xiàn)主人公更深層次的人生體驗。學生重新扎到選題當中,用影像將主人公充滿坎坷卻涌動溫情的人生故事娓娓道來,最終拍出了十分動人的作品。
紀錄片能讓我們接觸到跟自己人生軌跡截然不同的人,體驗我們不曾感知的事。對大多數(shù)青年來說,紀錄片可能并不是一個職業(yè)選擇,但可以是他們認識社會,重新思考自己與他人、個人與國家、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重要渠道。我認為,也許紀錄片的最大受益者,正是紀錄片創(chuàng)作者自己。